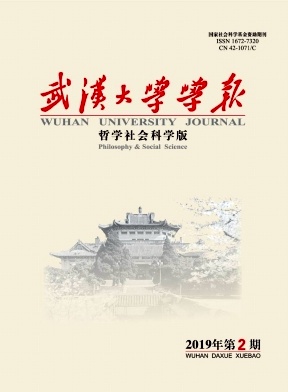
作者簡介:
胡象明,beat365英国官网网站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劉鵬,beat365英国官网网站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
摘要 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的成因和治理,是近年來公共管理學界讨論較多的問題之一。目前,無論在有關這方面的理論探讨中還是具體的實踐中,主要把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歸因于此類工程所引發的“事實風險”。而我們的研究發現,真正直接導緻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的原因,是由于利益相關者在價值觀上的差異所導緻的對上述事實風險的認知差異而可能産生的行為沖突,我們把這種風險稱為“價值風險”。事實風險隻是社會穩定風險形成的客觀基礎,價值風險才是其直接誘因。事實上,在目前我國有關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實踐中,也注意到了價值風險的治理,主要采取的措施如信息公開、适度增加補償等,但這些措施在實踐中可能會出現“現實悖論”,使具體的治理陷入困境。當然,通過對相關措施的進一步探索和完善,這種困境是有可能消除的,有關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也會得到更好的治理。
關鍵詞 敏感性工程;鄰避效應;社會穩定風險;價值沖突;治理困境
中圖分類号 D631.43;X820.4 文獻标識碼 A文章編号1672-7320(2019)02-0184-09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1&ZD173)
關于重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的研究在中國僅有10多年曆史,但研究成果豐碩,各級政府也相應出台了多項化解重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的政策,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重大工程中的特殊一類工程,即敏感性工程引發的社會沖突時有發生,已成為我國社會轉型時期遇到的難題,學術界從不同的視角開展研究,各級政府也在不斷創新方式方法化解此類矛盾,但收效不盡人意。在一些項目上,政府經常被迫采取“暫緩”或“停建”的方式平息沖突,對工程建設和行業發展極為不利。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面對敏感性工程建設遇到的突出問題,不能避而不談,更不能止步不前,必須堅持新的發展理念以破解困局。反思敏感性工程建設引發的社會沖突,不僅是發展過程中客觀存在的事實問題,而且與人們思想觀念的固化和對固有發展模式的依賴密切相關,也是主觀價值問題。為此,本文在結合“事實”和“價值”分析的基礎上,試圖結合對敏感性工程利益主體間主觀價值取向的分析,厘清敏感性工程中的事實風險和價值風險間的關系,以揭示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難以化解的根源及其治理困境。
一、事實與價值的結合:理解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成因的視角
現象與本質、客觀與主觀、事實與價值一直是西方哲學關注的焦點。古希臘哲學中愛利亞學派的代表人物巴門尼德最早提出“存在”的概念,第一次把世界分為現象和本質兩個部分,并進而采取人與自然二分法,讨論“人是什麼”“自然是什麼”,把主觀與客觀、本質與現象、價值與事實區分開來,使西方沿着自然主義和理性主義兩個方向推動着解釋自然界的理論不斷朝着日以精緻的方向發展。以儒、道兩家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則強調“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強調人應順應自然,符合自然規律。西方哲學講的人與自然二分法和中國古代哲學講的“天人合一”兩種不同的概念,影響着東西方人們思考問題、看待自然的方式。
西方學者按照自己的理論邏輯,從自然與人的二分法進一步發展為事實與價值的二分法。大衛·休谟在《人性論》中指出,“我們所确實知道的唯一存在物就是知覺,由于這些知覺借着意識直接呈現于我們,所以它們獲得了我們最強烈的認同,并且是我們一切結論的原始基礎。除了知覺以外,既然從來沒有其他存在物呈現于心中,所以我們可以在一些差異的知覺間觀察到一種結合或因果關系,但是永遠不能在知覺和對象之間觀察到這種關系。因此,我們永遠不能由知覺的存在或其任何性質形成關于對象存在的任何結論”。休谟認為,事實所表達的是“是什麼”的問題,而價值所表達的是主體所期望的事實“應當如何”的問題,而“應當如何”是主體按照自己的理解對事物進行的判斷。羅素認為,休谟把洛克和貝克萊的經驗主義哲學發展到了它的邏輯終局,從某種意義上講,他代表着一條死胡同,沿他的方向,不可能再往前進。德國哲學家亞瑟·叔本華受柏拉圖和康德等人的影響,反對理性主義并開創了非理性主義的先河,指出康德最大的功績不是他的認識論,而是劃分了表象和物自體之間的區别。按照康德将感性直觀和人的知性十二先驗範疇構成的經驗對象理論可推論出,表象世界成了既是直觀又是思維既非直觀又非思維的東西。叔本華認為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并指出一切事情都按照其嚴格的必然性而發生,人們所感覺到的自由意志仍是處于表象世界的活動,而所觀察到的任何表象以及人的任何行為都受到意志的控制。不管是休谟對經驗主義的發展到邏輯的終結,還是叔本華對理性主義的批判并開啟了非理性主義的先河,都回到人的主觀意識的世界,對客觀事實的判斷受到人主觀意識的影響,人的行動受到主觀意識的支配。此後,經過波普爾和羅爾斯等人的發展,堅持事實與價值分離,堅持把意義和價值作為研究對象的人文主義,堅持把經驗和事實作為研究對象的實證主義或科學主義朝着不同的方向發展。
實證主義或科學主義奉行馬克斯·韋伯提出的所謂“價值中立”的标準探索純粹事實世界。韋伯認為,科學家在研究過程中應隻遵循他所發現的資料,無論他的研究結果對自己或他人是否有利,都不能将自己的價值觀強加于資料。在一段時期内,價值中立被西方科學家所推崇,成為包括社會科學在内的西方科學研究中一個比較普遍性的方法論原則。但是關于價值中立也引起了學者的争論,認為通過所謂的價值中立不僅不能達到科學性,還會相反起到十分有害的結果。正如德懷特·沃爾多所言,科學隻關注事實,而無關于概念和理論,這一普遍謬論有賴于人們未能對表觀事實與表述事實加以區分,要得到脫離所有概念的純粹表觀事實,科學家隻能盯着他的數據,卻無法報告其觀察的結果。托馬斯·庫恩認為,不管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是一種被先例和傳統束縛的活動,他的每一次貢獻都是以過去的示範性成就或所謂“範式”為樣闆的,任何科學知識都不能簡單的從自然中讀取,它總是通過曆史上特定的和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範式來起媒介作用。康德講到,心靈能夠确定認識的隻是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置放進人類經驗的東西,在康德看來,純粹經驗帶給人類的知識不是基于經驗,而是先驗。由此判斷,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并不能擺脫固有範式或先驗的影響,難以實現價值中立。
綜上所述,在人們所認識的對象中,事實和價值總是結合在一起的。人們所認識的對象,首先是一個客觀世界,這個客觀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客觀存在的,這就是所謂的事實,它是科學認知的對象,也是人們需要改造的對象,同時還是人們賴以生存和生活的對象。然而這個對象又并非是純粹的客觀世界,人們在認知這個對象時,總離不開評價這個對象,從而使這個對象具有人為的主觀烙印。這是因為,人們在描述客觀世界、對客觀事物作出判斷的過程中受到主觀意識的支配。人類的主觀意識受到習慣、曆史、文化、社會階層、生物、語言、想象、情緒、個人無意識、集體無意識等多重因素的影響,而且可能被這些因素所扭曲。究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每一特定階層甚至特定環境下的個人都有可能形成自己特定的價值觀或認識事物的特定價值準則,而且這些價值觀或價值準則有可能是多元的,甚至是相互沖突的,人們在認識事物時,總要受這些特定價值觀或特定價值準則的影響。在不同價值準則指導下,不同人對同一客觀事物的認知,往往存在着主觀的認知差異。這種主觀認知差異部分是由認知者的認知能力、獲得信息等因素造成的,部分是因為價值觀的差别造成的。
關于事實與價值的理論分析,為我們理解敏感性工程及其社會穩定風險的成因提供了一個較好的理論視角。一方面,從事實層面來看,敏感性工程建設會給相關利益群體甚至全社會帶來事實上的利益,如核電站建設可以給地方政府帶來稅收,為當地增加就業,為社會提供清潔而價格低廉的能源,等等,但對部分人來說,特别是對核電站周邊的居民來說,存在環境與技術安全上的風險、利益損失上的風險等,應該說這些風險都是客觀存在的,可将他們稱為事實風險。另一方面,還有一種價值風險,或稱價值沖突的風險。當利益相關者之間存在價值沖突,對同樣的事實風險,持不同價值觀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認知。如在有關核電站的技術安全風險方面,核電專家認為,如果安全系數達到99.999%,當屬非常安全了,已經達到了技術安全的要求,不必擔心安全問題;但當地的居民則認為這個0.001%也是重要的安全隐患,因為對他們來說,一旦發生安全事故,其損失則是100%,他們也可能會為此采取某種抗議行為。可見,當工程周邊部分居民與地方政府或建設方存在價值沖突風險時,在有關客觀風險的認知上就可能存在認知沖突風險,進而産生雙方或多方的行為沖突風險;當這種風險達到一定程度時,就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從而形成一定的社會穩定風險。因此,從事實和價值兩方面結合來看,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的形成實際上有兩個風險源:一個是事實風險,一個是價值風險。從邏輯上講,事實風險是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形成的客觀基礎,但隻是間接的風險源;而價值風險是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形成的更直接的誘因,因而是直接風險源。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本質上是事實風險與價值風險的綜合體。隻有從這兩個風險源的角度來理解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的成因,我們才能對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的本質有更深刻的認識,從而對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的治理做出更深層次的思考。
二、價值沖突:敏感性工程的多元利益主體與多元價值取向
經濟發展使社會聯系更加緊密,相互間的影響突破了地域限制。大型敏感性工程作為人類改造自然的重要活動,其所涉及的利益群體呈多元化趨勢,尤其在互聯網影響如此廣泛的今天,一些旁觀者也會涉及其中,導緻原本簡單的社會沖突複雜化,牽扯進更多的利益主體。因利益主體間所處的社會地位、占有的資源、所處的環境不同,各利益主體因價值沖突相互論戰,甚至爆發沖突。根據對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多年的研究,敏感性工程涉及的利益主體可以歸納如下:一是政府。政府作為社會發展的主導者,是敏感性工程建設的決策者。一般來說,政府的價值取向傾向于公共利益。美國當代著名公共行政學家喬治·弗雷德裡克森指出,現代公共行政必須在政治、價值與倫理方面進行恰當的定位,從而構建公共行政官員所應遵循的價值規範與倫理準則,他認為政府官員的倫理價值應該是樂善好施,追求民衆的利益而非政府自身的利益。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表明我國政府在追求經濟發展過程中将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和協調發展,以人民美好生活為發展目标,謀求全社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二是企業。此處企業是指敏感性工程建設相關企業。作為敏感性工程的建設商,首先是追求企業自身的利潤,追求企業利益最大化。當然,我國的敏感性工程大多是由政府主導的項目,因此,要求企業除了追求其自身的利益外,還應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和公共福利。三是公衆。主要是指敏感性工程建設影響到的公衆,即敏感性工程的周邊民衆,工程的建設可能在經濟、環境、健康等方面對他們造成影響。作為受影響的群體,不僅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還會不同程度地顧及權利、地位、聲望、信任、安全等。随着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公衆從單純追求經濟利益也在向多元的價值追求轉變。四是其他利益組織。主要包括敏感性工程建設對其他行業發展造成不利影響而形成的組織和純粹與敏感性工程項目建設價值理念不合而形成的社會組織,如綠色和平組織、動物保護組織、海洋保護組織等。這些主體的價值取向往往取決于他們的理念和行業特征,如環保組織的價值取向可能是環境保護價值的最大化,動物保護組織的價值取向則是動物保護價值的最大化。以上通過對敏感性工程相關利益主體的分類,可以看出不同利益主體所處的角色不同,價值取向不同,成為不同利益主體間沖突的根源。當然,同一類主體中不同個體因其所處的環境、所具備的知識水平不同,也存在價值取向的差異。
大量的事實證明,敏感性工程利益主體間的價值沖突或在價值取向上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具體而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作為敏感性工程決策者的政府與工程周邊民衆在價值取向上的矛盾
作為敏感性工程建設的決策者,在價值取向上追求的是社會利益最大化。以核電站建設為例,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導緻電力需求增加,如果止步不前,電力供應無法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如一些城市在用電高峰期采取限電、停電等方式緩解用電壓力,如果政府不作為,經濟發展會受影響,同時受影響的公衆也會将矛頭指向政府。環境壓力又迫使政府不能無限制擴大火電規模,在水電、風電等利用受限的情況下,選擇核電不失為相對較好的方案。但是,核電站建設項目屬于典型的敏感性工程,其建設需要征地拆遷,還可能在環境安全等方面給工程周邊的民衆帶來負面影響,總之存在一些負外部效應。在此種情況下,政府在價值取向上可能要求當地居民“舍小家、顧大家”、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然而,作為核電站周邊的居民,至少有相當一部分人在價值取向上堅持個人利益須得到保障,甚至要求優先保障個人利益,或者如果負外部效應難以避免,就要求全社會或所有受益人平均分擔。因此,常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不管類似核電站的工程建在哪個地方,總會有“為什麼不建在他家附近而建在我家附近”的質疑聲。但政府在決策過程中,考慮工程建設的選址,不僅要注重社會公平,還要依據地質、氣象、水文等客觀事實條件進行成本核算。這樣,在兩種利益難以調和的情況下,這種價值取向的矛盾就會因利益沖突而導緻行為沖突。因此,在敏感性工程建設上,由于政府在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過程中,在負外部效應的分擔上并不能保證絕對的社會公平,甚至有可能存在一部分人利益受損的風險,從而導緻這一部分人的抵制。
(二)作為敏感性工程建設者的企業與工程周邊民衆在價值取向上的矛盾
作為工程建設和運營者的企業,其價值取向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而要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在産出一定的前提下,需要盡可能降低成本。對于核電站等這類特殊的敏感性工程來說,對環境安全和技術安全的保障投入十分必要。有關這類投入的價值取向,企業的安全價值觀往往是一種相對安全價值觀,即以達到現有的國家标準或國際标準為安全保障投入的基準,追求一種達到當前國家标準或國際标準的安全。然而,對于工程周邊的民衆來說,有關環境安全和技術安全的價值取向則是絕對的安全觀,要求企業在環境和技術方面提供絕對安全的保障。這對企業來說,不僅在技術上難以實現,在安全上的投入也不可能是無限的。據筆者所做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對“你認為最有可能成為誘發核事故的原因”這一問題的回答中,選擇技術缺陷的占31.8%,自然災害的占29.9%,人為失誤的占18.7%,蓄意破壞的占10.6%,其他的占9.0%,這反映出公衆對核電技術和其抵禦自然災害能力的擔憂是對核電安全擔憂的重要原因。在安全方面,公衆期望工程絕對安全,對生命财産沒有任何威脅。而在工程技術方面,則用可靠性來衡量工程質量、安全程度,人的操作失誤也是由人的不可靠造成的,可靠性并不是絕對的,存在一個最優解,是相對的可靠。在核電領域,将核事故分為設計基準事故和超設計基準事故,針對可能發生的設計基準事故,一般提前制定比較充分的應急預案;但發生概率極低的超設計基準事故,是無法預料到的。如果一味地追求絕對安全,企業的代價是巨大的,也并不一定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因此,敏感性工程在環境與技術方面的安全性與公衆所期待的絕對安全是有差距的,無法完全消除,因為任何工程建設都存在一定的安全風險,就像人們乘坐交通工具要承擔發生交通事故的風險一樣。
(三)公衆對敏感性工程在價值取向上的矛盾
敏感性工程建設,涉及一大批利益相關者,地方政府、投資和建設商、公衆。而公衆又可能具有雙重角色:作為公共受益人的社會公衆和作為可能承擔工程負外部效應的公衆,後者主要是工程周邊的居民,但他們同時也具有前者的角色,即公共受益人的角色。由于公衆具有這種矛盾性的雙重角色,他們在價值取向上往往也是矛盾的:作為公共受益人,他們支持這種具有較大公共利益的項目建設,也就是說,他們的價值取向與公共利益趨于一緻。但是,如果這個項目建在他們家附近,作為工程負外部效應的承擔者,他們反對這一項目的建設,即他們的價值取向與公共利益相背離。根據筆者所做的一項關于公衆對核設施建設支持度的調查結果顯示,有59.3%的公衆對核電的發展持樂觀态度,但真正支持核電建設的占比則隻有49.6%,而贊成在自己家鄉建設核電站的人數則進一步更是降到了45.8%。據此推斷,存在部分公衆認為敏感性工程——核電站對社會的發展有益,但又不支持核電建設;即使支持核電建設,也有部分人不支持在自己家鄉建設核電站。由此可見,相當部分人認為,“雖然敏感性工程是個好東西,但别靠近我”,這就是所謂的“鄰避效應”。在這部分人看來,敏感性工程不管靠近誰都會受到抵制,如果出現抵制意願強烈的個體,還可能會影響沉默的大多數,導緻“好東西”無法落地。這些抵制敏感性工程的部分公衆,由于其價值認知的不同,抵制理由也可能是不同的。一部分人可能出于尋求更多利益補償而抵制,如根據馬斯洛的層次需求理論,不同階層的公衆對補償的期望不同。還有一部分人,可能并非出于利益需求,而是因為某些社會、文化的原因而抵制這類工程建設,如核電站的建設可能會對當地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人文環境等帶來無法恢複的突變,有些人出于對原有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人文環境的适應或者依賴,對敏感性工程采取抵制行動。
(四)與敏感性工程建設利益相關的社會組織的價值取向和公共利益價值取向的矛盾
從經驗觀察中往往會看到這樣一些現象,在已發生的一些因敏感性工程建設引發的社會沖突事件中,常常會出現某些社會組織的身影,如環保組織、動物保護組織以及某些行業組織等。這些組織參與抵制敏感性工程建設,情況比較複雜,特别是在價值取向上也有所差異。例如,環保組織參與抵制某類敏感性工程建設,可能是出于他們對環保價值最大化的理念形成了本組織特有的價值取向,根據這種價值取向抵制一些在政府看來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敏感性工程建設項目,如城市垃圾處理場建設項目。此外,敏感性工程代表着一種新的發展方式,存在某些方面的弱點是在所難免的。而有些社會組織因發展理念的不同,從自身的價值取向出發,對此不能理解和接受而對敏感性工程建設産生抵制。根據多年的實證研究發現,在反對敏感性工程建設的過程中,甚至存在某些社會組織或專業人士利用科學的名義,對敏感性工程的弱點進行抨擊并放大以此争取更多的支持者,組成對敏感性工程的對抗組織,如“反核組織”“反垃圾焚燒組織”等。有些行業性的社會組織則有自己的行業價值取向,如煤炭類行業組織,則在價值取向上要求維護本行業的利益。如果建設核電站,對火電的需要将會減少,這對火電廠、煤炭企業及其産業鍊上的其他企業造成沖擊,這類人群出于對自身利益的維護,将會選擇抵制措施。
敏感性工程建設涉及多個利益相關主體,這些利益主體在如何對待敏感性工程建設問題上,分别具有自己的價值取向,而且各自的價值取向分别有自己的内容和特點,不同主體之間的價值取向存在着相互矛盾甚至相互沖突的可能性。由于各利益相關主體在價值取向上的不同,造成了他們對敏感性工程建設的态度不同。當這種不同導緻沖突時,就可能導緻各利益相關主體在如何對待敏感性工程建設問題上的行為沖突,這種沖突達到一定規模就可能危及社會穩定。因此,如果上述沖突的概率上升到一定限度,就可能形成敏感性工程建設的社會穩定風險。
正如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裡希·貝克在《風險社會》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伴随着工業社會的産生和發展,人類進入了風險社會時代。“在發達現代性中,财富的社會化生産與風險的社會化生産系統相伴随”。敏感性工程的建設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帶來一定的社會穩定風險,這一點已為學界普遍認可。但有關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的成因,目前學界有不同的認識,存在客觀歸因論和主觀歸因論的區分。客觀歸因論從事實出發,将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的産生歸因于工程客觀存在的風險,這樣的風險可以通過科學計算得到,風險大小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通過科學的方法和有效的措施可以将風險發生的概率降到最低,即使發生,也可以通過提前設置好的應急程序有效控制事故,并認為正是這種基于事實的客觀風險引發了社會穩定風險。主觀歸因論則從價值出發,将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的産生歸因于公衆的主觀感知風險,并且認為這種主觀感知風險受個人價值觀、知識水平、社會地位、觀念等的影響,感知風險的大小與工程實際風險大小可能并不一緻,工程對周圍經濟、環境、安全等影響的風險都是由個體主觀構建的。客觀歸因論忽視利益相關者的主觀感受和風險認知,不能理解社會穩定風險與公衆感知風險的關系,難以解釋公衆風險感知對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的影響,因而從調節公衆風險感知的角度提出有效化解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的策略。相反,主觀歸因論忽視了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産生的基于事實的客觀風險基礎,在對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進行測量時,因為個體風險感知易受到所處環境等易變因素影響,風險測量結果的随機性比較大,如福島事故前後,公衆對核電站風險認知就出現了很大差異。因此,單一的主觀歸因論也很難解釋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的客觀性和必然性,因而難以從客觀的利益關系、環境和技術層面的角度提出有效化解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的策略。
通過對敏感性工程利益主體間的價值沖突或在價值取向上的矛盾的具體分析進一步表明,敏感性工程确實存在事實風險,并且這種事實風險構成了社會穩定風險成因的客觀基礎;但是僅僅存在這種事實風險,并不一定會産生社會穩定風險,這隻是一個必要條件。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的産生還要有一個充分條件,這就是價值風險,隻有在事實風險與價值風險的雙重作用下,社會穩定風險才有可能形成。事實風險能夠解釋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生成的客觀基礎,這種事實風險作為客觀風險,是可以通過科學的手段進行測量和比較的,從而可以通過技術的手段降低和消除。價值風險能夠解釋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生成的主觀因素,即公衆認知風險,這種風險是根據公衆價值認知而對事實風險作出的評價,因為不同個體之間存在價值沖突,因而不同個體之間對同一事實風險的感知(即感知或認知風險)可能存在明顯差别,對于價值風險的化解,則隻有通過思想溝通和教育說服的方法才有可能化解。依此觀點出發,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的治理應包括以下兩個步驟:一是化解敏感性工程中的事實風險,也就是工程的客觀風險,可以通過技術進步等手段解決,這也是工程領域的技術專家一直在努力解決的問題,在此就不再贅述;二是化解敏感性工程中公衆的價值風險,對于這種風險的化解,僅僅依靠技術手段和技術專家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還需要心理專家、社會工作專家、社會風險評估和管理等方面專家的廣泛參與。化解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的關鍵是要化解公衆在敏感性工程問題上的價值沖突,使之從價值觀上高度認可敏感性工程建設的社會價值及其對自身的價值,并把敏感性工程的事實風險控制在公衆可接受的價值風險的範圍内。
三、治理困境:敏感性工程多元利益主體價值沖突化解的現實悖論
從目前我國敏感性工程建設的現狀來看,很多工程建設都受困于這種因多元主體間的價值沖突而導緻建設過程中主體間的行為沖突,最後因釀成較大的社會穩定風險而迫使工程下馬。近年來發生了不少此類事件,如2013年廣東鶴山反核事件和2016連雲港反核事件º。這類事件的出現,往往使在建工程陷入了極度困境,導緻工程擱淺,嚴重的會使工程建設停止,甚至取消原有規劃,往往會對國家、地方和建設商造成嚴重損失。為走出這一困境,針對敏感性工程建設引發的社會沖突,我國各級政府高度重視,出台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2005年,四川省遂甯市率先頒布了《重大工程建設項目穩定風險預測評估制度》,随後其他各地也出台了各具特色的評估模式。2010年,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建立健全重大工程項目建設和重大政策制定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2011年,中央開始全面推進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工作,對涉及群衆切身利益的重大工程項目和重大政策,在決策前實行經濟效益和社會穩定風險“雙評估”制度。201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建立健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的指導意見(試行)》(中辦發[2012]2号)。同年8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布了《國家發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資産投資項目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暫行辦法》(發改投資[2012]2492号)。2017年,國務院發布了《重大行政決策程序暫行條例》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公衆意見。我國各級地方政府也在積極落實中央有關決策,制定适用于本地區的風險防範和化解措施。
但是,這些措施的效果依然非常有限。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這些措施更多注重的是事實風險層面的評估和防治,而對于價值風險層面的評估和防治則顯然做得不夠。從我國目前絕大多數對大型工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報告來看,主要是注重評估敏感性工程的事實風險,如對當地經濟、環境、安全的影響,力求對客觀事實風險作出科學的評估。評估的目的是從客觀事實出發分析工程對當地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影響,試圖采取措施将工程帶來的不利影響控制到最低限度,以争取公衆的支持。如在安全方面,如果工程絕對安全、有益無害,則很容易通過評估并獲得公衆支持。然而,任何工程,尤其是敏感性工程卻難以達到上述完美的程度,就像核電站,即使發生事故的概率極低,但隻要發生的可能性存在就無法完全消除公衆的疑慮,評估采用什麼标準、标準能否獲得一緻認可,就蘊藏着客觀事實之外的主觀價值分歧。因此,對敏感性工程事實風險進行評估是解決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的必要但并非充分的條件。
上述分析表明,如果不化解敏感性工程相關利益主體間的價值沖突,就很難對敏感性工程的社會穩定風險進行有效治理。那麼,應如何化解敏感性工程相關利益主體間的價值沖突呢?目前在現實中一般采用兩種策略:一是公開信息的策略,即在工程建設開工之前或在決策過程中對與工程相關的、涉及周邊居民利益的信息予以公開,以保障利益相關者的知情權,讓利益相關各方充分表達意見,并在決策中盡可能對各方意見進行整合,從而使利益相關各方在相互了解中達到價值取向上的相互認同;二是增加利益補償的策略,即當認為自己利益因工程建設受損的一方表達強烈不滿時,政府或工程建設方采取對認為自己利益受損并強烈不滿的一方增加補償,以消除其不滿,從而換取其對工程建設的支持。
從理論上講,以上兩種策略的設計也許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理性原則,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則陷入了難以解決的悖論。
先看信息公開的策略。在一定意義上,政府作為決策者采用這種策略,也是應公衆要求所緻。因為如果在敏感性工程決策過程中或建設開工前,政府不公布相關信息,不讓與工程相關的利益主體表達利益訴求,當工程開工時,一些對工程建設不滿的利益相關人會以侵犯其知情權為借口,對工程建設表達強烈不滿,并采取抵制行為,還會影響部分不明真相的公衆卷入抵制行動中。但是,如果在決策過程中或在工程開工前就公開信息,則常常是沒等到工程開工的那一天,對工程抵制的行動就開始了,同樣導緻工程無法開工。因此,在信息公開問題上,常常會導緻作為決策者的地方政府不知如何是好,一時難以做出決定。
再看增加補償策略。在敏感性工程建設過程中,必然會涉及拆遷、征地等利益問題,對于被拆遷、征地的對象給予必要的補償是應該的,但是如何補償的問題則是非常複雜的問題,因為利益補償而引起對工程建設的抵制行為的事件,這樣的例子太多。在利益補償中,如果政府采取統一标準補償,例如對征收的土地采取每畝同等價格的補償,這樣補償工作非常簡單,但會引起一部分認為自己土地比人家土地肥沃的人對補償不滿,因為畢竟土地肥沃程度不同、收益不同而造成被征收者的損益不盡相同。為解決這個問題,制定适當有差别的補償标準是必要的,但如果地方政府或開發商對那些認為自己承包土地相對肥沃并對原補償不滿的人不适當地增加補償,則有可能會進一步激發被補償者要求增加補償的欲望,甚至永遠無法達到其所期望的目标,以至于出現某些“釘子戶”。這種現象在房屋拆遷中表現得非常明顯。
上述分析表明,在我國目前治理敏感性工程建設中利益主體間價值沖突的策略中,存在着兩個明顯的現實悖論,到目前為止,還尚未找到有效解決這兩個悖論的辦法。前面已指出,敏感性工程多元利益主體間的價值沖突或矛盾是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的成因之一,而且是一種更直接的成因。因此,要化解敏感性工程的社會穩定風險,就有必要化解敏感性工程建設中利益主體間的價值沖突。然而,由于在現有的化解敏感性工程利益主體間價值沖突的策略中,常常存在着悖論,這就使我國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的治理陷入了相對難以化解的困境之中。我們之所以說是一種相對難以化解的困境,是因為以上所揭示的化解敏感性工程利益主體間價值沖突策略中的悖論隻是以上已有策略的悖論,并不意味着敏感性工程利益主體間價值沖突的化解存在着邏輯上不可克服的悖論。如果我們能找出新的、更有效策略,也許敏感性工程利益主體間價值沖突能夠有效化解,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的治理困境會随之而解。當然,有關敏感性工程利益主體之間的價值沖突或矛盾不可能絕對消除,隻可能是相對減少。從這個意義上說,敏感性社會穩定風險的治理也是相對的,風險不能徹底消除,但可以化解到可控程度。
四、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解釋了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有兩個風險源:一是事實風險,即敏感性工程建設客觀上存在利益風險、環境與技術的安全風險等,這些風險是引發其社會穩定風險的客觀基礎。但隻有基礎,并不一定能直接生成社會穩定風險。二是價值風險,因為不同利益相關者價值觀的不同,導緻他們對事實風險認知不同,從而直接引發其社會穩定風險。我們對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成因的分析,目的是進一步探讨化解社會穩定風險的措施。從邏輯上講,要化解敏感性社會穩定風險,必須化解作為其社會穩定風險源的事實風險和價值風險。然而,在事實風險層面,通過技術和相關制度安排,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這種風險,但永遠無法使這種風險完全消除;在價值風險層面,目前正在探索各種化解措施,但就目前常常采用的兩種措施而言,即信息公開和增加補償措施,有可能造成現實悖論,從而使有關治理陷入困境。但是,這種困境僅僅表明現有措施存在不完善之處,并不意味着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的治理成為不可能。其實,隻要我們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不斷總結經驗,就一定會不斷發現新治理方法和手段,不斷完善已有的治理方法和手段,以最低成本、最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使敏感性工程社會穩定風險得到更好的治理。
(本文轉自《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
